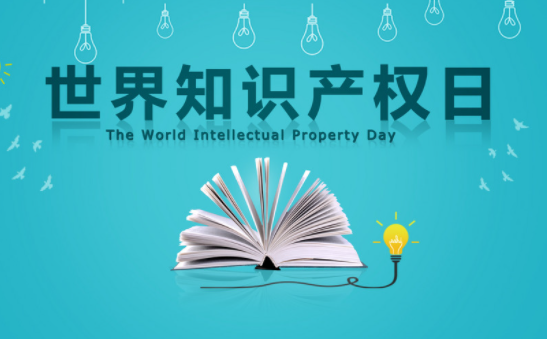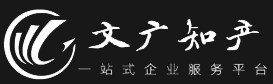涉案作品即"金丝贴先师孔子"的版权纠纷案
录入编辑:安徽文广 | 发布时间:2023-04-08
涉案作品即"金丝贴先师孔子"的版权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705号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简称华夏工艺研究所)因与被申请人李某某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三终字第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事实依据
华夏工艺研究所申请再审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关于"对于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依据版权证即可认定其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不仅提供了涉案作品即"金丝贴先师孔子"的版权证,还提供了涉案作品样本、说明书、《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改制协议,一审法院还直接调取了版权登记档案证据,华夏工艺研究所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的证据充分。2.一审判决关于"涉案作品是原华夏工艺研究所经营期间由李福生独立创作完成"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3.一审判决关于"原告认可被告提供的《大众日报》等相关报纸中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报道内容均突出指向李福生开发研制了金丝彩贴画"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从未认可案外人李福生(即李某某的父亲)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仅认可《大众日报》等资料的真实性,《大众日报》报道的内容是金丝彩贴画,不是涉案作品,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无视华夏工艺研究所证据,对法院直接调取的版权登记档案证据的内容及证明事项未做任何评判,对本案关键证据如《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置若罔闻。
(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关于"可以证明李福生享有'金丝贴'工艺专利权"和"诸多新闻报道均记载是李福生开发研制了'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的认定缺乏证据。1994年至1997年,李福生一直是华夏工艺研究所成员。金丝贴是李福生离开华夏工艺研究所后诞生的。任何新闻报道都没有"李福生开发研制了'金丝贴先师孔子'作品"的记载。2.二审判决关于"证据3系华夏工艺研究所合伙期间的规定,因该研究所已拆伙,而拆伙协议未对作品归属进行约定,故该规定与本案无关"的认定歪曲事实,且缺乏证据。1998年经体改委和主管单位正式批准,华夏工艺研究所由原集体所有制企业改为民营独资企业,华夏工艺研究所没有拆伙。证据3即《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形成于1995年5月20日,涉案作品完成时间为1995年5月。虽然《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并非仅为涉案作品而制定,但完全适用于涉案作品。(三)华夏工艺研究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在本院审查期间,为了证明金丝彩贴权属归华夏工艺研究所,华夏工艺研究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成果名称为"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获得的《第45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奖》《科技进步二等奖》《科技进步三等奖》《97中国(泰山)专利技术及新产品博览会金奖》等证书,1997年版金丝彩贴画单页,1998年版三折说明书内页(展录了"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获奖情况),《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书》。华夏工艺研究所还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1751号行政判决书,用于证明李福生未获国家专利,不是"金丝彩贴发明人"。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其向一、二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和上述新证据完全可以证实华夏工艺研究所享有"金丝贴先师孔子"著作权。
本院认为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华夏工艺研究所是否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
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其提供的涉案作品版权证、样本、说明书、《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改制协议和一审法院直接调取的涉案作品版权登记档案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经查,涉案作品版权证是华夏工艺研究所于2008年5月26日向德州市新闻出版局申请登记取得的,华夏工艺研究所申请版权登记时填写的《作品登记表》中显示"金丝贴先师孔子"的作者为华夏工艺研究所和赵振利,《作品登记表》中所含的《"金丝贴先师孔子"说明书》《作品自愿登记权利保证书》《作品版权登记协议》、"金丝贴先师孔子"样稿均由华夏工艺研究所单方提供。李某某对华夏工艺研究所主张涉案作品著作权归其所有提出异议并提供了反驳证据。在此情况下,应当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判断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本案中,华夏工艺研究所现任负责人赵振利与李福生于1995年3月14日签订的《协议》第6条规定:"分工:生(指李福生)拥有金丝贴专利权,且有绘画、设计和工艺技术之特长,宜分管工艺开发研究和生产。利在金丝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关键时期起了重要作用,且在公关和管理方面有特长,宜担当经营管理方案的主设计和涉外协调事宜"。《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载明如下信息,成果名称为"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完成单位为"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主要研制人员名单(××)为"李福生",鉴定日期为"1995年5月7日"。
上述两份证据充分证明李福生具有创作涉案作品的能力。李某某提供的1995年9月16日《大众日报》第一版的一篇报道记载:"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李福生大胆创新,开发研制出集工笔画、布贴画、镶嵌工艺、沥粉贴金等艺术特点融为一体的金丝彩贴高级装饰画,今年获国家发明专利"。该报道同时刊载了一幅照片,照片中李福生等人手持一幅孔子画像,但因图为黑白色,无法辨识照片中孔子像的整体色彩搭配情况。李某某还提供了上述报道中所刊登照片原件,亦为黑白照片。华夏工艺研究所关于该报道与本案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李某某还提供了1995年8月30日《德城报》,该报第一版题为"德州金丝彩贴饮誉海内外"的报道有如下记载:"金丝彩贴高级装饰画,是由德州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总工艺师李福生开发研制的纯手工艺品,获得国家专利"。综合考虑上述证据,二审判决认为华夏工艺研究所不能证明其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并无不妥。
华夏工艺研究所在本案二审开庭时还提交了两份《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一份为手写件,上有李福生的签名,落款日期为1995年5月20日;另一份为电脑打印件,右下角有赵玉海签名和华夏工艺研究所公章,落款日期为1995年5月20日。李某某当庭辩称,并非李福生签名,即便是李福生签的字,这也是合伙期间的规定,还有拆伙协议。经二审法院释明,华夏工艺研究所未对签名是否属实申请鉴定。李福生、赵振利、赵玉海三人于1997年9月25日签订的拆伙协议书对原研究所的货物、固定资产、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但未对作品归属作出约定。二审判决记载了李某某对《关于作品问题的规定》的质证意见后认为,因该研究所已拆伙,而拆伙协议未对作品归属进行约定,故该规定与本案无关。二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
华夏工艺研究所向本院提供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在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6日第二次开庭时已经由李某某向法院提交过,根据该鉴定证书载明的成果名称、完成单位、主要研制人员名单、鉴定日期等信息,该鉴定证书无法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反而证明李福生具有完成涉案作品的能力。华夏工艺研究所提交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获奖证书针对的均是"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而非针对涉案作品著作权。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另案作出的(2012)高行终字第1751号行政判决书,李福生主张其就"金丝彩贴"已经在先申请了专利,但承认未取得专利授权,这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权属也没有关系。1997年版金丝彩贴画单页、1998年版三折说明书内页上附有"先师孔子行教像",此两份证据只能说明"先师孔子行教像"曾经是华夏工艺研究所的产品,并不能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华夏工艺研究所不能证明其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认定。《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书》载明如下信息,项目名称为"金丝彩贴画及其制作工艺",主要完成单位为"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主要完成人为"李福生",申报日期为"1996年5月7日",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华夏工艺研究所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反而证明李福生具有完成涉案作品的能力。华夏工艺研究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推翻二审判决的认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判决结果
驳回德州市华夏民间工艺研究所的再审申请。
欢迎你来到安徽文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网站,如有知识产权相关疑问,可以随时联系知识产权专业老师,联系方式13965191860(微信同号),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