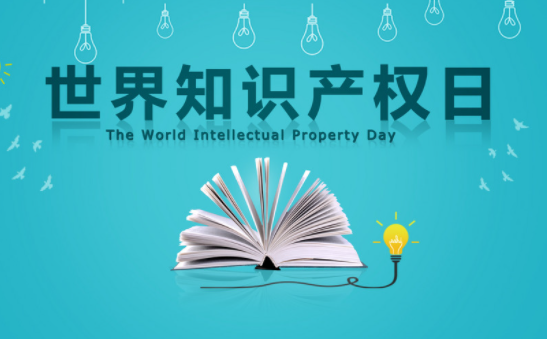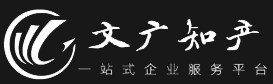不良影响判断主体的确定
录入编辑:安徽文广 | 发布时间:2024-05-22
不良影响判断主体的确定
——评析上海城隍珠宝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案
本案要旨 特定商标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应当根据不良影响的具体类型,以相关领域的特定主体为判断标准,而非以相关公众或者一般公众为判断主体。相应地,对于具有多种含义的商标标志,如果其中一种含义具有不良影响,则该商标标志整体即应被认定为具有不良影响而不应作为商标使用。
案情 1997年8月,上海城隍珠宝总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提出第1218394号“城隍”商标(下称争议商标)的注册申请,并于1998年10月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14类宝石、金刚石、珍珠(珠宝)、翡翠、玉雕、戒指(珠宝)、手镯(珠宝)、项链(宝石)、贵金属耳环、银饰品等商品上。2010年11月,争议商标经商标局核准转让给上海城隍珠宝有限公司(下称城隍公司)。
2009年6月,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豫园公司)针对争议商标提出撤销申请,主要理由是:“城隍”是道教神灵的名称,是道教信徒普遍尊奉的偶像,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严重伤害了道教界的宗教感情,具有不良影响;争议商标亦与豫园公司长期使用并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老城隍庙”商标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请求按照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下称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撤销争议商标的注册。
2013年3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13〕第07311号《关于第1218394号“城隍”商标争议裁定书》(下称第7311号裁定)。该裁定认为:豫园公司关于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请求已超过了5年时间,故对该项撤销理由不予支持。豫园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城隍”是道教神灵的名称,是道教信徒普遍尊奉的偶像,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有害于宗教感情,具有不良影响,已构成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的情形。据此,商评委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 城隍公司不服第7311号裁定,提起行政诉讼。 经查,《辞海》中载明“城隍”的含义为:(1)护城河;(2)古代神话所传守护城池的神。道教尊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另据豫园公司提交的《道教大辞典》《中国城隍信仰》《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等证据以及城隍公司提交的《道教神灵谱系简论》等证据的记载,城隍作为神灵的历史悠久,是与老百姓关系比较密切的神灵,道教以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 2011年5月,商标局作出商标驰字[2011]第130号《关于认定“城隍”及第1120085号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的批复》(下称第130号批复),认定“城隍”商标为驰名商标。二审诉讼中,商标局向法院复函,确认第130号批复是以该案争议商标为基础认定“城隍”商标为驰名商标的。
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城隍作为道教信仰中常见的神灵,是道教信徒普遍尊奉的偶像。将“城隍”注册在宝石、金刚石、珍珠(珠宝)等商品上有害于宗教感情,具有不良影响,已构成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第7311号裁定。城隍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城隍”具有“护城河”等含义,但除此之外,“城隍”也被用来指代道教的特定神灵。在此情形下,将“城隍”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将对信奉道教的相关公众的宗教感情产生伤害,并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争议商标的注册使用违反了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应予撤销。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虽然应当考虑相关商业标志的市场知名度,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的市场秩序,但这种对市场客观实际的尊重不应违背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在争议商标违反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情况下,即使争议商标经使用具有了较高知名度甚至曾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也不应因此而损害法律规定的严肃性和确定性。综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通常认为,商标标志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应当根据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加以审查判断。但是,对于诉争商标是否具有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判断的主体。
根据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的商标法(下称第三次修正的商标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提出注册申请。”因此,在具体案件中,申请注册或者被提出异议、争议(适用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情形)、无效宣告(适用第三次修正的商标法情形)或撤销的商标,总是与具体商品联系在一起的,即诉争的商标总是有其相关公众的。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规定,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显然,不良影响的判断主体与案件中具体诉争商标的相关公众通常是存在差异的。此时,在对诉争商标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响进行判断时,就存在多种选择:相关公众、一般公众以及相关领域的特定群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因此,在商标法领域内,相关公众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特指案件中具体的诉争商标所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与此相反,一般公众则不限于诉争商标所指定使用的商品类别,泛指社会上的普通民众。
笔者认为,就不良影响的认定,由于涉及不良影响的情形多种多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多方面,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相关公众或者一般公众为判断主体。相关商标或其构成要素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应当根据其涉及的不良影响的具体类型,以其相关领域的特定群体为判断主体。比如该案中,判断争议商标是否具有宗教方面的不良影响,就应当以特定宗教的信众为判断主体,看争议商标作为商标使用是否会损害该领域特定群体的宗教感情。
之所以将相关领域的特定群体作为判断主体,原因在于不良影响的判断不同于商标显著特征的认定。显著特征强调的是商标具有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因此必然是和具体的商品或者服务类别联系在一起的;而不良影响并不以商品或者服务的类别为限,只要相关商标标志或其构成要素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就应当被认定为具有不良影响。所以,相关公众这一主体概念并不适用于不良影响的判断。但是,由于认识水平、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领域的社会公众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不能以一般公众的这一不作任何区分的主体作为判断特定商标标志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准。判断是否具有不良影响仍应当区分不同类型,以其对应的特定领域的特定群体为准,只要该特定群体认为诉争商标标志或其构成要素具有不良影响,就可以认定该商标标志具有不良影响。
由于不良影响的认定应当根据其具体类型,以相关领域的特定群体为判断依据,所以,该特定群体基于其认识水平、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往往只了解或者只关注相关商标标志多种含义中的一种或者几种含义,而如果该含义对这类特定群体而言具有不良影响,则该商标标志是否还同时具有其他含义,已不影响对该商标标志整体上是否具有不良影响的判断。以该案为例,虽然“城隍”具有“护城河”的含义,但对于信奉道教的广大信众而言,“城隍”已被用于指代该宗教中的特定神灵,作为商标使用显然是有损于其宗教信仰的。所以,即使争议商标标志还具有其他含义,也仍然要被认定为具有不良影响而不适宜作为商标使用。
法谚有云:“法律顾及衡平。”又云:“人民之安宁乃最高之法律。”对于经过使用具有一定知名度甚至较高知名度的商标,虽然其完全具备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但是,如果在其识别作用发挥的同时,会带给相关领域特定群体以消极、负面影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则无论该特定群体与该商标的相关公众在范围上是否存在重合,都应当顾及该特定群体的利益,在商标识别作用与社会公共福祉之间求得平衡。所以,该案中,即使争议商标曾经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也因其会损害特定宗教信众的宗教感情而最终被商评委和法院撤销注册。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